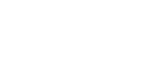後疫情時代下國家的公共治理挑戰-以法國為例
世界衛生組織於2023年5月宣佈結束新冠肺炎的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全球正式來到後疫情時代,從過去的封控轉為鬆綁,不僅影響全球與區域治理,也開啟各國的公共治理新問題。過往的區域整合強調跨層級治理(gouvernance…

政府與議員在質詢時的攻防戰
地方議會的表現對於臺灣的民主品質相當重要(黃秀端,2018),這主要是因為縣市議員在議會中,對於預算法案的審查和地方首長、行政官員的監督,對地方自治的成效和品質有著重大的影響。在議員監督行政機關的工具和方式中,質詢是議員經常使用的方式之一,也是民眾較為關注的工具之一。因此,本文試圖整理過去關於議員質詢的文獻,並結合作者過去的實證研究,簡要介紹關於議員質詢相關的研究和發展。 議員質詢的相關研究 過去學者對於議員質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議員的提問方面(Questions),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研究試圖分析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並探討哪些因素或具有哪些特性的議員會提出更多的質詢問題。實證研究顯示反對黨議員傾向於提出更多的質詢問題(Proksch…

漢堡港城的永續發展與社會治理
2015年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希望2030年能夠達成17項目標,包括終結貧窮、性別平權與消除飢餓等,由於氣候變遷影響,永續城鄉及氣候行動等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的項目(UNDP, 2022a)。Hiromi…

誰作球我打:議員質詢的資訊從何而來?
議員質詢,是民主制度中重要的監督工具,也是民眾日常會重視與關心的行為之一。每逢施政總質詢時,議員質詢的行為總會受到媒體關注。例如,某直轄市議員在質詢時,常會贈送市長禮物,以諷刺他的施政與個人行為;曾有某縣議員在質詢時,拿出毒品當作道具,因觸犯法律而被裁罰,引起全國注意;另外,有些議員在質詢時使用尖銳的言語,使政府官員無言以對。議員的這些質詢行為,經過媒體報導後,往往成為茶餘飯後的熱話。那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議員質詢的內容,資訊是從哪裡來?作者繼上次介紹質詢的不同形式,包括口頭與書面質詢的目的、功能與差異外(見議員質詢:表演還是實事求是?),本文試圖從學術觀點,探討議員質詢的內容,並以資訊政治學的觀點,剖析議員質詢的內容會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資訊政治學的觀點 在台灣,不同縣市的口頭質詢時間各有差異。例如,台北市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間為40分鐘,苗栗縣則是45分鐘。在有限的時間裡,議員不可能無止盡地提出問題。議員問些什麼問題,取決於其所關注的議題,以及資訊的掌握程度。以資訊政治學(politics…

議員質詢:表演還是實事求是?
臺北市議會在3月下旬陸續開始市政總質詢,王世堅議員在質詢時贈送柯文哲市長一件「我就爛」T恤,以表達對市長的不滿。經過媒體報導後成為了茶餘飯後話題。每當新聞報導後,總有人批評說,議員是在表演,嘩眾取寵。因此,本文試圖從學術觀點簡單探討,議員質詢究竟是表演還是實事求是?且有何功能?…

法國媒體眼中的臺灣防疫作為
2019年末新冠肺炎爆發造成全球諸多影響與困擾,大部分國家面臨疫情擴散與經濟消退等問題,臺灣的防疫措施得宜,有效阻止疫情擴散,發揮強大的工業與社會能量,將防疫所需用品輸往海外,展現“Taiwan…

跨區的地方治理願景
當代治理型態逐漸轉為服務取向的後官僚組織模式,強調彈性的原則制度以及組織分工,使得多層次治理以及跨域合作的動員方式受到高度關注且蓬勃發展。其中,大型開發計畫具備整合統一目標、建立作業項目的特徵,利於跨越各區域相互箝制的制度性障礙,在兌現項目願景的前提下,達到跨域治理的實踐意涵。本文章將從…

地方領導的未來
政治制度要長期成功運轉其一特點是在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有體制創新及按組織需要進行改革,以及能面對新的問題及需求時做出有效的治理,地方領導是達成上述目標的重要人物,這尤其在疫情嚴峻的今日更能體悟此重要性。因此,本文以Bentzen,…

地方議員對會議的想像
在議事廳打架、出位的言行、唱歌演戲、咄咄逼人又或是專業問政⋯⋯,這些可能都是大家對於議員開議的印象。隨著民主化進程,政治代議取代過去威權體制的一言堂,人民透過民主選舉制度選出代議士並為其發聲及履行公共事務。當中不論是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他們為了履行人民委託並獲得下一次選舉的勝利,其必須進行選區服務及透過不同的立法行為為民服務,當中包括在審查法案、質詢、提案及投票等,因此會議成了議員重要的任務。因此,本文借助Freeman(2020)的研究向讀者們簡單介紹會議的類型有哪些,以及會議是如何運行的? 議員角色 研究議員的行為與角色,最根本的假設在於議員以連任為最主要目的(Mayhew,…

英國如何提升地方民主
政治與社會若要發展和進步,強健的參政機制是不可或缺的,而良善的民主不只需要人民廣泛地進行政治參與,同時也仰賴多元的政治甄補(Political…